良渚玉(良渚玉琮)
良渚先民既无温饱之虞,自然会产生精神领域的某种追求。如果以遗址发现地的代表性文物来命名,良渚文化或可称得上是“玉文化”。其玉器数量之丰、品类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国史前文明阶段,无出其右者。
>良渚玉(良渚玉琮)
良渚文化冠形器(亦称玉梳背),高4.2厘米,宽3.85厘米,出土于浙江杭州反山。该器为片状梯形,中部有大眼阔鼻浮雕兽面纹,嘴扁而宽,眼廓、鼻、嘴皆饰细阴线纹,样式精美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工艺最复杂,形制纹饰最富有地区特色的首推玉琮。玉琮的形制变化最多,大别之有二,一是内外皆圆的圆筒形:二是外方内圆的方柱形。前者是玉琮的早期形式;后者则比较多见,但直到《古玉图考》的考证,才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原来正是先秦经籍中所称的“琮”。玉琮的节数没有定数,早期多一二节,晚期可多到十多节。玉琮都有“饕餮纹”或“兽面纹”等纹饰,早期纹饰较繁,越到后来越简化,有些晚期玉琮只刻两个小圆圈。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器表都雕成四个凸面和四个凹面,凹凸相间对称。这种装饰图案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换句话说,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在出土的良渚文化众多玉琮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当推1987年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那件“玉琮之王”。其制作技术如此高超,称得上是鬼斧神工。琮上雕刻线条纤细如发丝,最精绝一处竟然在一毫米的宽度内刻出了四五条线来,着实叹为观止。玉琮用料为坚硬的矿物,在良渚文化时期,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不会冶炼硬金属,当时的工匠们可能就是用装柄加固的燧石打制成的石钻与鲨鱼牙齿之类的简易工具,创造出了精美的玉器,令人惊叹。
“玉”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既如此之高,反山第12号墓就显得更加异乎寻常了。这里出土了大名鼎鼎的“玉琮之王”,也不缺罕见的玉钺(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其余玉璧及其他最高品质的随葬品则象征着财富。同时握有“神权”“军权”与巨额财富代表的无上“族权”的墓主人会是什么人?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因此就说,“一手把持这样三种权力君临良渚社会的人物称之为王,怎么看都是合适的。”
良渚文化的玉钺,出土于浙江杭州反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良渚文化玉钺一般有长方梯形玉钺和扁方梯形玉钺两种类型,其最高格式一般由钺身、冠饰、端饰三部分组成,在良渚文化中,玉钺与玉琮、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是显贵者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
良渚社会是否已经跨过了国家的门槛,拥有了一位“国王”?
在很长时间内,学界将良渚社会判定为“酋邦”。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作为复杂或发达的酋邦毫无问题。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还提到,“良渚也不能被简单地安置在国家社会的文明系列里,良渚缺少国家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书写记录的文字系统,虽然已是国家社会的秘鲁印加文明也没有什么书写的文字系统,但他们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尽管现代人对此很难理解。又比如国王的问题??我不确定良渚存在的是酋长还是国王。不过,通常来说,一个国王应该有王冠之类的标志物,虽然我们不能总期待王冠的出现,但国王应该有自己办公的地方,应该有宫殿。”
然而,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考古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位于良渚遗址群的莫角山中心遗址正是宫殿性质的基址!
莫角山修建时景象复原
分析植物苞粉等环境考古学成果之后得知,四五千年前太湖流域的气候与今天相差不多,同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而湖沼湿地的面积大于今天,如今湖荡密布、水网交错的“江南水乡”在当时更像是一片湖沼平原。良渚先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并重塑了地形,将河道挖深,将湿地堆高,除了水网及湖面,几乎都是土筑台地。
莫角山“宫城”所在的良渚古城同样也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先生的计算,包括“内城”与“外城”与水坝坝体在内的施工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眼下的中国第一高楼,高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的土方量也不过60多万立方米,尚不足良渚古城的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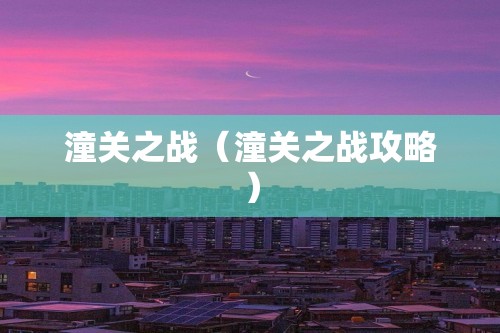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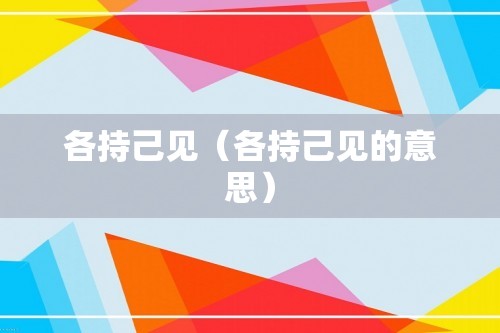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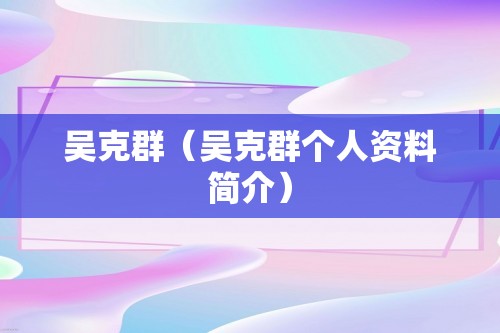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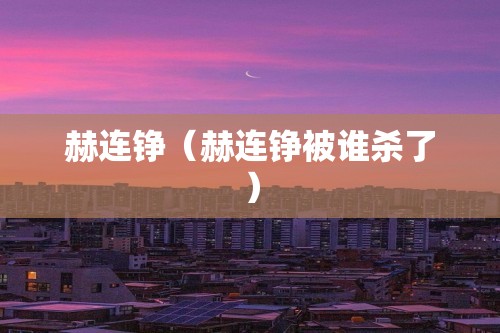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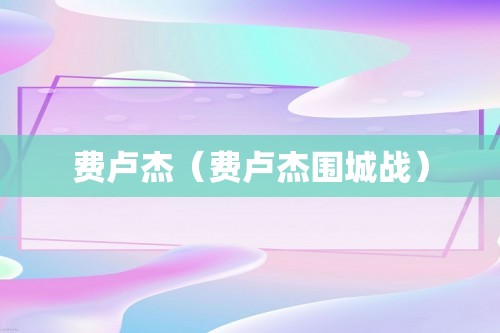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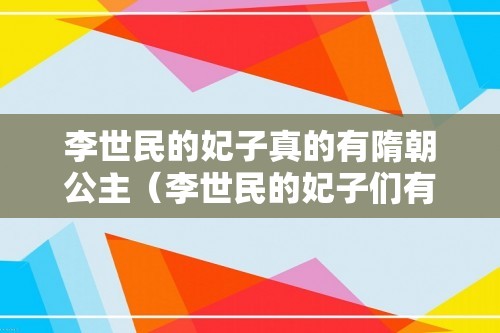
0 条评论